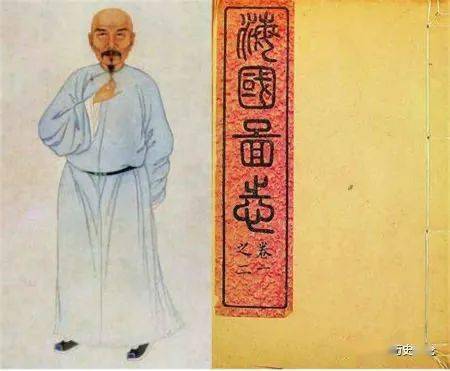|
沿着技能、技艺的概念理解方式,麦克劳务派遣传统的“技术”与当下的“技术”仍存在一致性。从相关概念构成的概念群来看,古代中国多元的“技术”概念包“技”“机”“器”“术”等多种概念以及它们的衍生概念。古代社会的技术水平尚不发达,古人围绕“技术”概念群展开的思考亦称不上体系化,但是古代中国的技术思想具有引人注目的特色和值得重视的价值。“尽管中国古代技术是在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由于注重技术发展与自然、社会、伦理、人的身心关系等相关要素的和谐,传统文化中包含很多有关技术的本质、技术与生态关系、技术的社会影响、技术伦理、技术认知过程等方面的思想资源。”虽然已经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古代技术哲学(思想史)研究进行探索并创造出一些有分量的成果,新近由陈凡和朱春艳主编的《技术哲学思想史》辟有两章,分别论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技术哲学思想和中国当代技术哲学思想。更早的专门研究比如王前和金福《中国技术思想史论》、王前《“道”“技”之间:中国文化背景的技术哲学》等。但是有关于此的挖掘尤其是思想特色和当代价值方面的深挖任重而道远。 西方学者也注意到中国思想史视域内关于技术的人文反思“有某种领先地位”。米切姆(CarlMitcham)早在1998年就提出:“ 中国文明的伟大特征之一是,它不仅创造了许多技术,而且也首先对那些技术进行了批判思考。”从米切姆上溯至海德格尔,都不约而同地论及《庄子》。《庄子》所阐述的“技”与“道”关系也是古代中国由技能、技艺来理解传统“技术”概念内涵的典型代表。庖丁解牛的故事中,庄子借庖丁之口说明“技”与“道”的联系:“ 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技”的次序为末,但可以通往最高境界的“道”。
与此相反,将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的观念传统也在《庄子》中有所体现。“ 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依赖“机械”(技术)的“机事”和“机心”终将背“道”而驰。为了避免“道之所不载”的后果,即使知晓技术的好处也不该使用技术。“机”概念所反映的技术观就是认为技术自身缺乏内在的原则、理性,与“道”各执一端。那么,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庄子》的技术观就是拒斥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主张停留于原始朴素的本真状态呢? 上述看法无疑是片面的,《庄子》的技术观需要更全面的解读。庄子还依次阐释了“德”“道”“事”“技”的涵义:“ 故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从末端的“技”出发,可以依次分别觅得“事”“义”“德”“道”“天”的属性。“ 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因此“技”与“道”具有内在关联,“技”并不意味着背离“道”,而是可以追求“道”。从“道”俯视“技”,两者构成一种向下兼容的关系。在此种意义上而言,传统的“技术”概念规定了技术在存在论层面的秩序,避免了“技术失控”“技术替代”等滑向“人化自然”的异化危机,而是与“道法自然”并行不悖。 二、近代的“技术”概念:外来的和产业的 在近代中国遭逢巨变和科技转型的宏观背景下,“技术”概念也随之发生“范式转换”,是串联起传统“技术”概念与当下“技术”概念的关键中间一环。正是在这个承前启后的时期,“技术”概念实现与“technology”的相互对应并成为日常话语中的高频词汇。马西尼(FedericoMasini)研究现代汉语词汇形成时关注到近代中国人首先将“technology”翻译为“艺学”,将该词列入“本族新词”。“艺学”意即工艺、技艺,“本族新词”意即中国人于“19世纪创造的真正的新词”。此外,刘正埮等编纂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不仅未收录“艺学”,而且未将“技术”视为汉语外来词。这些汉语外来词研究的经典作品无法化解“技术”概念自身存在的牴牾,与后来尽人皆知的情形相比,源自古代中国的传统“技术”概念原本并不流行且不对应“technology”。随之而来的问题在于,近代的转变何时发生?如何发生? 事实上,在19世纪中国人将“technology”翻译为“艺学”的同时,日本人已将其翻译为“技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技术”概念常见于日本的各类著述之中。例如,日本司法省明法寮编纂的《第二宪法类编》中有“测量技术”“电信技术”的说法;小山健三译纂的《化学分析法》中有“分析技术”“技术实验”的说法;1887年(明治二十年)日本颁布《技术官等任用条规》,主要规定了奏任官和判任官两种形式技术官的任用方法。显而易见,近代日本使用的“技术”概念不同于古代中国的传统“技术”概念,而是对应于“technology”。作为日式译词的“技术”后来传入中国,构成中国近代“技术”概念完成转变的来源。 “技术”概念与日本息息相关的外来特征可从多个方面予以证明。一是词源,黄河清《近现代辞源》列出“技术”最早的两处源头均指向日本,分别是1884年姚文栋译《日本地理兵要》中的“航海、造船、测量诸技术”和1889年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中的“事务官、技术官”。二是时间,“技术”概念在中国的流行大约始于20世纪初,与甲午后学习日本浪潮的兴起时间相一致。以《申报》全文检索“技术”为例,1870年代为8次,1880年代为18次,1890年代为28次,1900年代为96次,1910年代为720次。三是用法,近代中国师法日本之处甚多,比如前文两次述及的“技术官”。民初文官体系内所设一类就是技术官,其中分技监、技正、技士等。 外来的“技术”概念不属于新造的词汇,而是以旧词添新义,很难说是完全意义上的日源汉语外来词。因为“技术”概念在中国古已有之,虽然其内涵至近代发生转变,但仍存在一致性,技能、技艺的理解方式亦仍延续。不过近代中国“技术”概念的外来特征是毋庸置疑的,并随之带来其它新的概念特征。例如,1946年“中国技术协会”在上海成立。该协会“ 脱胎于前工余联谊社,曾办工业讲座多次,及‘上海工业品展览会’一次,最近并恢复发行《工程界》月刊”。从名称看,“技术”由“工业”演进而来。两年后,该协会在国立交通大学(今上海交大)举行年会的同时举办了“工业技术展览会”,展览会的“ 电机、机械、纺织、化学、原子能等部,分由电机学会、机械学会、纺织学会、化学学会、数理学会等负责”。无论是该协会的前身名称还是组成学科,都能反映出“技术”概念与“工业”“工程”等产业类概念的亲缘关系,足见“技术”概念的产业化特征。 旧词添新义会导致概念演进的两种结果:新旧交替或者新旧并存。与“技术”密切相关的“科学”概念在古代中国主要是指科举之学,在近代中国则转变为日式译词,对应于“science”。新内涵完全取代了旧内涵,当下的“科学”概念已没有科举之学的意思。“旧”的部分与“新”的部分在近代中国的“技术”概念内则并没有交替或割裂,而是处于共存状态。从“旧”的部分来看,与古代传统相比,近代“技术”概念摈弃了方技、术数内涵,仍承载技能、技艺内涵。魏源提出的著名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实际就是对传统“技术”概念的化用,并传递出重要信息:将“技术”从思想体系的最末端推向危机变局的最前沿,进一步巩固强化了被广泛认可的中国技术实用主义传统。此外,近代“技术”概念也泛指技巧、方法,如“立身之技术者,即教人以立身处世之方”,内涵得以拓展。
从“新”的部分来看,近代“技术”概念因旧词添新义才趋于流行。外来的和产业的两大概念特征折射出技术在中国的深层变化,蕴含着多重根本性的意义转折。首先是从古典意义到现代意义的转折。传统和近代的“技术”概念分别是古典意义和现代意义上的。“如果不阐明现代技术与先前的技术形态在质上的差异,就无从恰当地确立现代技术的地位。”古典与现代的性质差异也关系到后两种意义转折。其次是从地方意义到普遍意义的转折。传统的“技术”概念是地方性的,适用于古代中国的本土语境,无法和“technology”或类似英文词汇对应。近代的“技术”概念则是现代的、全球的、通用的。最后是从理念意义到实体意义的转折。传统的“技术”概念是相对抽象的,可理解为“坐而论道”。近代“技术”概念新产生的内涵是产业技术,呼应于同时期中国艰难起步的工业化进程,亦伴随着技术产业、技术工人、技术教育等相应环节的共同推进。 三、当下的“技术”概念:科学化的和泛在的 外来的“技术”概念流行其实也意味着中国技术的发展与全球技术的发展渐趋并轨,因此考察当代中国的技术概念及事业首先离不开世界技术史的广阔视野。20世纪中叶以来,电子计算机技术、核技术、航天技术等高新技术的突飞猛进为当下的“技术”概念提供了再次变革的契机。21世纪以来,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新兴、前沿和交叉领域的加速发展更促使人们将目光聚焦于技术,深入思考技术与社会、技术与人等主题。在技术威力和影响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当下的“技术”概念凸显出科学化的和泛在的两大特征。 站在技术一侧评估技术与科学的关系,技术科学化和科学技术一体化是当代技术发展的显著趋势。技术与科学之间在古代无甚关系,它们的相互作用与交融从近代以来就开始了。“科学过去是躲在经验技术的隐蔽角落辛勤工作,当它走到前面传递而且高举火炬的时候,科学时代就可以说已经开始了。”两者相提并论时科学通常被置于技术之前,科学与技术的一体化表现为基础理论与应用手段的关系。相左的观点则认为技术在科学之前,不是技术科学化而是科学技术化。“许多科学理论,恰恰是靠了技术的力量(比如实现了实际应用、设计出重要实验等)才得以发展或被证实的。”技术与科学何者为先?是否为平行系统?都是讨论技术与科学关系时经常涉及又难以给出排他性答案的问题。 进而言之,若欲探讨技术科学化和科学技术一体化,则无须纠缠于彻底澄清技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无论持何种观点,都或多或少地承认当代技术与科学存在紧密关联,科学技术一体化仍大体成立。从技术科学化来看,“我们应当看到现代技术科学化的事实,同时也应当看到现代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的”。即便从科学技术化来看,“所谓科学技术化就意味着科学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技术,并受技术的制约”。以此为例,当代中国的第一代技术哲学家们就已特别注重从技术与科学的关系层面进行双向论证,在承认技术与科学密不可分的现实基础之上论说技术。 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态势在概念层面表现得更为突出,亦可佐证“技术”概念是科学化的。“科技”概念诞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后,原先是种概念“科学”和“技术”组合而成的属概念,后来作为“科学技术”的缩略术语而变得越来越流行。如1951年燕羽所编一本小册子《中国历史上的科技人物》认为“ 中国科技的落后,究亦只是近代的事情”。对于“科技”概念的流行有不少批判观点,然而批判者更关注“科学”而非“技术”,更关注技术性的科学而非科学性的技术,对于科学性技术或者说技术科学化的反对意见甚少。 官方语境的“科技”和“技术”概念也偏向于科学性技术或者说技术科学化。其一是“科技”概念下的“技术”概念。“技术”概念在当代中国被纳入“科技事业”的整体政策话语之中,而“科技事业”的方向性表述是“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无论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经典论断,还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政策话语体系内“科技”的落脚点都在于“致用”的“技术”。其二是“技术”概念自身。一面作为基础理论的“科学”为作为应用手段的“技术”提供源头活水。与应用手段“核心技术的根源问题是基础研究问题,基础研究搞不好,应用技术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面作为应用手段的“技术”以其实践成效为评价标准。“核心技术研发的最终结果,不应只是技术报告、科研论文、实验室样品,而应是市场产品、技术实力、产业实力。”
芒福德 当下“技术”概念的另一大特征是泛在性。泛在(ubiquitous)即无所不在,原系信息技术领域的概念。从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andsociety,STS)的视角来看,技术的泛在性是技术造就人机物三元融合和万物智能互联的必然结果。稍早前的技术哲学家们在进行技术批判时已经对此有所觉察,如海德格尔的“座驾”、芒福德(LewisMumford)的“巨机器”等。“ 技术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是人类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择、智能活动和奋斗的结果。”技术关系到人类文明的过去和未来,其在当代的泛在性亦表现为深度科技化的趋势。何谓深度科技化?“从当代技术演化进程来看,深度科技化是科技一体化与控制论观念相结合的产物,世界与人的有目的的技术重构和再造因而成为可能。”泛在的技术促使世界向人类进一步敞开,人类受益于高新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大大拓展了认知能力与范围,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 四、“技术”概念在中国演进的线索与启示 概念史尤其涉及近代史者面貌多变,情形复杂,研究难度不容小觑。刘正埮曾转引叶斯柏森(OttoJespersen)的说法:“ 我们在处理日语来源的汉语外来词时就有杯中糖茶交融之感。”考察“技术”概念即是在破解“杯中糖茶交融”的表象,不仅要对概念的出现时间、文献出处、内涵差异等庞杂内容加以梳理辨析,而且得根据主题需要和行文尺度进行选择性的总结提炼,通过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方式抓住概念演进的关键线索并获取思想启示。惟有如此,方能以概念为原点,选取作为“打开方式”的研究路径,让复杂、深厚、生动的历史人物、事件及思想为之“敞开”。 总的来看,“技术”概念在中国演进经历传统、近代与当下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皆呈现若干主要特征。上述主要特征只是选取了部分特征,当然无法涵盖“技术”概念的全部特征。但是由此书写的概念演进史自成体系,对应于三个阶段的线索为工匠技术、产业技术与科学化技术。依托传统-工匠技术、近代-产业技术、当下-科学化技术的关键线索,“技术”概念在中国的演进研究至少还可汲取出概念自身、历史维度和哲学维度的三点启示: 第一,“技术”概念在中国的演进研究愈来愈指向广义技术的见解。传统的“技术”概念虽然是多元的,但都未超越把技术视为手段的工具论见解和把技术视为人类活动的人类学见解。当下的“技术”概念是泛在的,已经从狭义技术的见解扩张为广义技术的见解。正如温纳(LangdonWinner)评价埃吕尔(JacquesEllul)关于技术的理性方法综合的定义:“ 埃吕尔的‘技术’与我们的技术一样,都指向一个广博、多样、无所不在的整体,伫立于现代文化的中心。两者均包括我们所造物体与所做事情的很大一部分。”技术是斯蒂格勒为之定义的“可能性”,亦是围绕目的实现的各种序列。中国是产业技术和科学化技术的后发国家,但也有希望实现后来居上。可预见的是,随着现代技术在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对于“技术”概念的诠释尤其是对于概念内涵与特征的诠释将继续更新甚至取得主导话语权,并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典资源实现古为今用。 第二,“技术”概念在中国的演进研究将为思考中国近现代技术(科技)思想史分期问题提供裨益。既有关于中国近现代技术(科技)思想史的专门研究为数不多,对分期问题的讨论更是寥寥,可见相关者如吴敬熙认为中国近代技术史和中国现代技术史以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界。历史分期是相对的,取决于采用何种分期标准。分期标准决定了历史分期的合理性和权威性,而历史分期决定了历史书写“说什么”和“怎么说”。基于近代“技术”概念和当下“技术”概念的演进及特征,可以尝试性地给出中国近现代技术(科技)思想史的分期。 时期之一是从1840年到1900年前后,也就是以鸦片战争作为西力冲击的标志性事件,而以甲午后的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作为转折。学习日本的风气使得作为日式译词的“技术”传入中国并流行起来,由近代“技术”概念取代传统“技术”概念的转变象征着技术思想的转变。时期之二是从1900年前后到1949年,主要经历清末、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三个阶段。虽然期间时局多变,但以宏观视野来看“技术”概念还是外来的和产业的,技术思想也主要建立于移植西方的基础之上。时期之三是从1949年至今,新中国成立后的“技术”概念趋向科学化的和泛在的,技术思想也随之变得更前沿、更丰富。 第三,“技术”概念在中国的演进研究将有助于促进中国技术哲学的新时代发展。一方面,技术哲学的研究传统向来偏向于西方的而非中国的,偏向于现代的而非近代或古代的。另一方面,深度科技化的当今时代呼唤作为“第一哲学”的技术哲学,以追问“技术向何处去、人文科学向何处去以及人类向何处去”这类根本问题。面对中国技术哲学现状与愿景之间存在的这种张力,植根于中国“技术”概念演进史的技术哲学研究既是必要的基础,也是推进的开端。从“技术”概念出发可以解读和阐发技术哲学的许多基本问题,如技术的本质、技术与科学的关系、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技术的价值负载、技术的设计、技术的风险及治理,等等。 当下全球技术哲学界讨论的一大热点就是高新技术的伦理问题。如若联系“技术”概念在中国的演进历程来看,中国思想史视域内的技术观没有技术万能或技术至上的传统,而是追求“熟能生巧”和“技近乎道”的境界。或许其弊病在于存在视技术为“本末”之“末”的鄙夷心态,但近代以来中国人认识到技不如人以后已经彻底转变心态,重视技术的专业主义因而兴起。“ 它一方面是强调追求应用性知识技能,另一方面是分工、专精理念的兴起。”技术的概念和实体都是有边界的。外来的“技术”概念必须本土化,泛在的“技术”概念离不开现实考量。今人既不能把技术当成“万能钥匙”,也不能因技术存在风险而因噎废食。对于技术研发及应用始终采取乐观而审慎的立场,摆正其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应当是新时代中国持续推动引领技术“向上”和“向善”的一贯之道。 (责任编辑:) |